【编者按】
由四川大学古籍所编纂的线装版《儒藏精华》共计36函260册,日前正式出版发行,向党的十九大献上了一份厚礼。《儒藏精华》于《儒藏》基础上萃取精华而成,按照计划,明年将完成共计600余册《儒藏》的全部编纂与出版工作。川版《儒藏》是当代学人在整理国故上的新贡献,也是对蜀学悠久治学传统的继承与接力。本文将告诉我们,世代蜀学在整理儒学文献方面是如何“接着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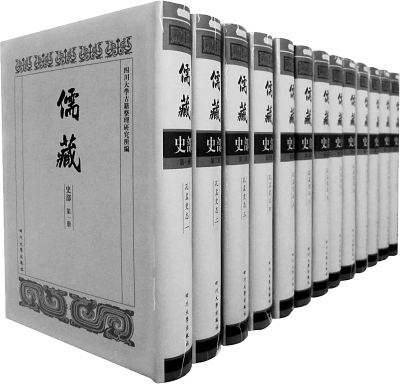
蜀学是发生在巴蜀大地,曾经与中原学术并行发展,最终影响并融入中华学术宝库的区域性学术。蜀学在其产生和演变、发展的历程中,与儒家经典和儒学文献,曾发生过非常密切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儒家经典体系的嬗变和定型,其成功经验和学术成果至今仍然是我们编好《儒藏》的精神食粮。
早在上古时期,这里便诞生了为儒、道、墨三家共同推崇的“生于石纽”(《孟子》佚文)、“兴于西羌”(《史记·六国年表》)的大禹,《尚书》载其因治水需要而悟“九畴”,于是衍为《洪范》(见《尚书》);又因伏羲氏《河图》,于是演为“三易”之首的《连山》(《山海经》佚文),两书及其所含“阴阳”观念和“五行”学说,奠定了后世中国(特别是儒家)经典文献的基本形态和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至于孔子所赞大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的孝道观念,以及《考工记》所载“夏后氏世室”的宗庙制度,更是后世儒家坚决持守的道德伦理和礼仪基础。约当殷商时期的“三星堆”遗址,所出土青铜祭坛,明显表现出“三界”(天、地、人)合一的信仰体系。战国时成书的《世本》又揭示蜀为“人皇之后”(《华阳国志》则称蜀“肇于人皇”之际),天皇、地皇、人皇三才一统的观念,又与三星堆出土青铜器吻合起来。《华阳国志》记载蜀王亡故,不同中原之谥号,而以“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黄帝”命其庙号,又与《洪范》中所载五行相生相克的观念结合起来。至于禹所娶涂山氏之婢女吟唱“候人兮猗”的《南音》,后为周公、召公所取法“以为《周南》《召南》”(《吕氏春秋·音初》);又为屈原所依仿,造为楚辞(谢无量《蜀学会叙》)。所有这些,均可视为早期巴蜀学人对儒学经典文献形成的特别贡献。
秦汉时期,物华天宝的巴蜀地区不仅是祖国统一的坚强基地,也是中华学术孕育和发展的摇篮。汉景帝末年,庐江舒城人文翁为蜀守,有感于秦后天下绝学,乃修起学宫于成都市中,派张宽等18人前往长安从博士讲习孔子“七经”(在中央所传《诗》《书》《易》《礼》《春秋》之外另加《论语》《孝经》),张宽等学成归来,即居学宫教授;文翁复选下县弟子入石室肄业,成功改变巴蜀的“蛮夷风”,实现移风易俗,儒学正式扎根巴蜀。巴蜀士子,或负笈万里,求学京师,或居乡开馆,传道授徒,形成颇具特色的“蜀学”流派,史书或称“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汉书·循吏传》),或直接说“蜀学比于齐鲁”(《三国志·蜀书》《华阳国志》)。巴蜀士子以经学为学习和追迹对象,在儒家故里之外又形成一个儒化地区,故当时巴蜀有“西南邹鲁”“岷峨洙泗”之称。文翁石室是汉朝首个由地方政府建设的高等学府,在历史上成绩卓著,影响深远,史称“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汉书·地理志》)。汉武帝推广其经验,“令天下皆置学校官”(同上),于是汉代遍开郡国之学,中国进入全面“儒化”时代。当时汉博士所守经典为《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蜀中所传则是“七经”,在“五经”外增加《论语》《孝经》,形成“蜀学”重视伦理教化的经典特色。“七经”概念在东汉得到普遍认同,儒经体系于此实现从“五经”(重史)向“七经”(重传记)的转型。
东汉末年,天下纷乱,中央太学,徒具故事。然而时镇巴蜀的河间人高却在成都大兴文教,既恢复被战乱所毁的文翁石室,又在石室之东新建祭祀周公、孔子等历代圣贤的“周公礼殿”,教育与祭祀并重,形成中国学校“庙学合一”“知信合一”的体制,这比北魏在都城洛阳实行的同一制度提前300年!
唐自武后,滥用威权,学官多授亲信,太学形同虚设,但是远在西南的巴蜀地区,却社会稳定,人文辐辏。八世纪,成都诞生了以“西川印子”命名的雕版印刷物,肇开人类印刷术之先河,宋人有曰:“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朱翌《猗觉寮杂记》)五代时期,巴蜀图书出版成绩卓著,后蜀宰相毋昭裔于广政元年(938)倡刻《石室十三经》,历180余年至北宋宣和五年(1123),最后一经《孟子》入刻。蜀石经有经有注,规模宏大,“碑越千数”(晁公武说),堪称中国“石经”之最。蜀石经可贵之处,是在唐代盛行的“九经”(《易》《书》《诗》“三礼”“三传”)体系(即使《开成石经》刻了十二部,也只称《石壁九经》)外,增加《论语》《孝经》《尔雅》和《孟子》,以《石室十三经》(或《蜀刻十三经》)命名(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曾宏父《石刻铺叙》),正式形成“十三经”体系。这套刻在石头上的经书,促成了儒家《十三经》的最后形成。毋氏还将原来用于“阴阳杂书”和佛家读本的雕版技术,移刻儒家经典以及《文选》、类书等正规文献,为五代、北宋儒经“监本”等权威刻本树立了榜样。
宋代“四川”刻书业十分发达,“蜀版”是当时学人和藏家努力罗致和收藏的珍品,杨慎有“宋世书传,蜀本最善”(《丹铅续录》卷六)之说;开宝年间由政府主刻的多达13万片的“开宝大藏经”,即由高品张从信督刊于成都,成为后世藏经鼻祖。南宋理宗时,蜀人魏了翁将唐孔颖达、贾公彦等《九经注疏》删节为《九经要义》,以便学人。
明代,曾为四川右参政、按察使的曹学佺,既纂辑巴蜀掌故资料成《蜀中广记》108卷,又感于“二氏有藏,吾儒何独无”,“欲修《儒藏》与鼎立,采撷四库书,因类分辑,十有余年,功未及竣”(《明史》本传)。清乾隆中,在周永年重倡“儒藏说”的同时,四川罗江人李调元独自辑刻《函海》,收书150余种,许多稀见的儒学著作得以保存。晚清经学殿军廖平严分经史,善说古今,发凡起例,撰《群经凡例》,欲以今古文学为标准,撰著《十八经注疏》,以纠正东汉以下注疏今古无别、学派不清(如《十三经注疏》)的状况。近代,曾任四川存古学堂督监(院正)的蜀中才子谢无量,曾倡议编刻《蜀藏》;辛亥遗老胡淦诸人,又计划编纂“四川丛书”,只可惜皆因时势不济而未成。
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近代“蜀学”发祥地的四川大学,再度提出了儒学文献整理和体系重建的问题,那就是《儒藏》编纂。承担《儒藏》编纂的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自1983年成立以来,上继文翁石室“七经”教育之遗泽,下承蜀刻“十三经”、廖平“十八经”之余绪,在前辈学人组织完成《汉语大字典》《全宋文》等大型辞书和总集之后,又于1997年发起了“儒学文献调查整理和《中华儒藏》编纂”工程。针对当时中国文化品牌常常被域外国家抢注的现象,为保护儒学知识产权,川大学人特向国家商标总局申请“儒藏”商标注册,向四川省新闻出版局申请《儒藏》著作权登记。
编纂《儒藏》,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编好。虽然历代学人都有儒学文献整理的实践,如唐修《九经正义》、宋刊《十三经注疏》、明纂《四书五经大全》、清成《通志堂经解》和《皇清经解》(正续编),但却没有总汇儒学各类文献而成《儒藏》的先例。明朝万历中后期,孙羽侯、曹学佺曾先后提出《儒藏》编纂设想,却无具体编纂方案;清周永年、刘因等再倡“儒藏说”,也没有留下相应成果,其经验和体例都无从参考。
为取得《儒藏》编纂的学术支撑,川大学人申请了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哲学研究中心的重大项目“儒家文献学研究”,对儒学文献源流和演变轨迹、文献类型、重要典籍进行系统探索,撰成240余万字的《儒藏文献通论》,为《儒藏》编纂做足前期学术储备。同时,针对中国儒学大师辈出、流派众多的历史,为摸清儒家学人的师传授受、学术阵营和学派特征等情况,我们还联合港台学人组织实施了“历代学案”整理和补编工作。该项目对前人所编五种学案(唐晏《两汉三国学案》、黄宗羲《宋元学案》、王梓材等《宋元学案补遗》、黄宗羲《明儒学案》、徐世昌《清儒学案》)重新进行校勘,对前人未编的时段进行补编(《周秦学案》《魏晋学案》《南朝学案》《北朝学案》《隋唐五代学案》),共形成《中国儒学通案》十种,形成脉络贯通、传记齐全的全景式“儒学流派通史”。
有了对儒学文献的总体了解和儒学发展史的脉络把握,就大致具备了从事《儒藏》编纂所需的文献学知识和学术史背景。再参考《道藏》“三洞四辅十二类”、《大藏经》的“经律论”等方法,初步将《儒藏》按“经、论、史”三大类区分:《经藏》收录儒学经典及其为经典所作的各种注解、训释著作,包括元典、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孝经、四书、尔雅、群经、谶纬等11目;《论藏》收录儒学理论性著作,包括儒家、性理、礼教、政治、杂论等5目;《史藏》收录儒学史料著作,包括孔孟、学案、碑传、史传、年谱、别史、礼乐、杂史等8目。共计“三藏二十四目”。这样专题清晰,类属明备,既照顾到儒学文献的历史实际,也方便当代学人的翻检和阅读。
鉴于二十世纪以来人们对儒学历史存在隔膜,也为了给学界提供儒学史研究的系统资料,川大《儒藏》首先启动了“史部”编纂。自2005年出版首批《孔孟史志》(13册)、《历代学案》(23册)、《儒林碑传》(14册)以来,陆续于2007年、2009年、2010年、2014年,分四次出版了《年谱》《史传》《学校》《礼乐》《杂史》等类,至2015年年初,《儒藏》史部274册已全部出齐,实现了2500余年儒学史料的首次结集。其后又于2016年、2017年,出版“经部”86册;全套650册,将于2018年出齐。
在编纂体例上,本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理念,我们试图将入选《儒藏》的书籍,按一定体例编录,使其更具系统性,遵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别录》《七略》,清《四库全书总目》的传统,于《儒藏》开篇设《总序》一篇,三藏各立《分序》,小类各设《小序》,每书前又加《提要》。试图通过这些叙录的介绍和勾连,将各自成书的儒学文献联系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和完整的体系下,使《儒藏》成为“用文献构建的儒学大厦”。
千年儒学,百年沧桑。面对儒学不振、花果飘零、文献残破、学科无归的状况,重新回顾蜀学先贤从事儒学文献研究的学术实践,对我们研究和重审儒学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以系统体例编纂《儒藏》,不仅有利于儒学成果保存推广,而且有利于儒学学科重建、儒学价值重估,特别是儒家学术的再创造和再发展。以儒学为本位、以文献为载体,以“三藏二十四目”为纽带,通过重新构建儒家文献体系,达到恢复儒学大厦的效果,从而找回儒学文献的经典地位和学术价值,必将为儒学的当代传承和发展找到突破口。